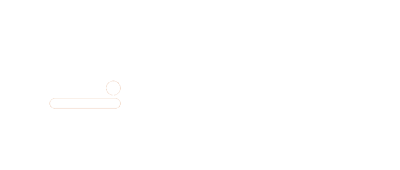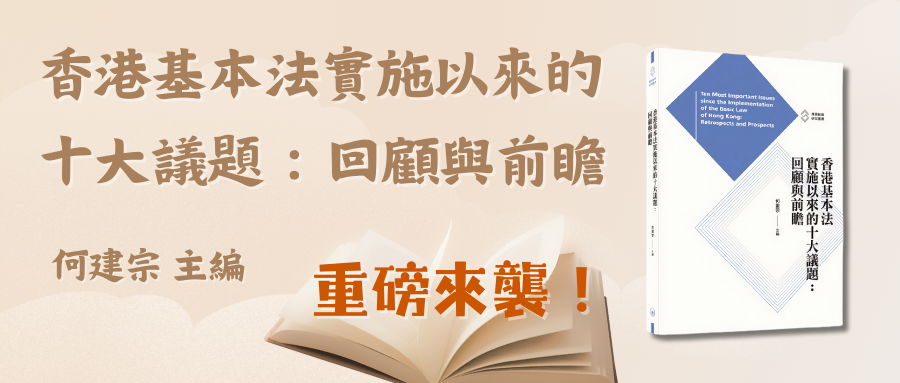何建宗、施漢銘:從美國司法案例 看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的關係

林至穎 : 百年變局,香港何從

林至穎 : 延選舉專注疫戰 保醫護救經濟

一直以來,維護國家安全是各國政府的重要和基本義務。只有維護國家安全,方可令整個社會處於正常的秩序下平穩地發展。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論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還是西方大國的美國都是一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51條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Haig v. Agee一案中也明確指出:「沒有比國家安全更為緊迫的政府利益,這是明顯而無可爭辯的。」
與國安衝突時 言論自由會出現限制
同樣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之一的言論自由,在眾多國家也被視為一項憲法賦予及保障的權利。作為香港憲制性文件的《基本法》第27條也指出「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指出「國會不得制定……剝削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
然而,以上兩種對國家及公民都至關重要的利益,在今天這個分裂、恐怖主義萌生和蔓延、國家安全經常受到挑戰及威脅的社會中頻頻發生衝突。由於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不可能考慮所有未來發生的可能情况、法律制定與社會發展的不一致性及法律語言的模糊性等因素,法定權利的界限在立法時未必能被界定清楚,而導致權利上的衝突。從美國的司法判例中不難看見,「言論自由」的「自由」並不是毫無界限的,往往在與「國家安全」產生衝突時,該項自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限制。
1969年判決:傾向保障言論自由
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對言論自由的權利作出了強而有力的保障,但是在多年來的司法實踐中,美國法律界對其是否應該存在界限及如何界定界限,一直存在爭議。當中最為經典的案例之一為「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 Ohio,以下稱「Brandenburg案」)。在Brandenburg案中,被告Brandenburg為美國俄亥俄州3K黨(Ku Klux Klan)的一名領袖,他在1964年透過電視傳媒辱罵黑人及猶太人,並揚言:「如果我們的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繼續壓制高加索白種人,我們將採取某些報復行動。我們有40萬人,將於7月4日向國會進軍。」其後,他被指控違反俄亥俄州的《組織犯罪防治法》(the Ohio Criminal Syndicalism statute)中以「犯罪、破壞、暴力或非法恐怖主義手段達成政治改革」,並判處1000美元罰款及10年監禁。
Brandenburg其後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院在判决中對非法言論的範圍作出限縮,推翻了州立法院的原判,並且認為該州的《組織犯罪防治法》違憲。法院使用了「煽動測試」標準限制公權力對言論的定罪,指出政府若要對煽動性言論作出定罪,必須符合兩個法定條件:(1)該言論是以煽動他人「即時」地違法或產生「即時」的非法行動為目的;(2)很有可能會煽動或產生這種違法行為,才可以對其進行限制。簡單而言,當時美國法院在「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中更為傾向於保障後者,只有符合嚴格的法定條件時,公權力才可對言論自由作出限制。
2010年判決:尊重國會和政府反恐判斷
然而,美國法院對於由Brandenburg案開始形成的高度保護言論自由原則在2010年的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案有所改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非法言論」的限制進一步擴大。被告「人道主義法律項目」(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是一個設立於美國的組織,為庫爾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an Kurdistan)和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支持者。以上組織分別爭取庫爾德人脫離土耳其和泰米爾人脫離斯里蘭卡獨立。儘管兩個組織從事的活動,例如政治和人道主義活動並非違法,但是因為曾執行了數次恐怖襲擊,導致包括有美國公民在內的傷亡,因而被美國政府界定為「境外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該案中,被告Humanitarian Law Project希望透過捐款和為該等組織提供法律意見及援助的形式,協助它們日常合法及非暴力的運作,被指違反了美國反恐怖法案(18 U. S. C. 2339)規定的「任何人向指定的『境外恐怖組織』提供『服務』或『物質支持』均屬犯罪」。
本案的爭議點在於,被告在已知對方為美國國務院定義的「境外恐怖組織」的情况下,向這些組織提供「訓練、專家建議和協助、服務和人員」從事人道和非暴力活動是否違法;若是,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這些訓練包括教導成員以國際法來和平解決爭端,向聯合國和其他組織游說等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判決被告有罪,並同意國會的解釋,即外國恐怖組織的罪行是如此敗壞,任何對它們的支持(哪怕是對所謂非暴力活動的支持)都會促進其恐怖主義活動。而證據顯示,恐怖主義組織並沒有在運作上和財政上為其人道和非暴力活動與恐怖主義活動之間設立防火牆。最後,法院承認,由於它在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上缺乏專業知識,而反恐威脅的工作往往難以取得足夠資料,恐怖活動的後果難以評估。因此反恐工作更多是基於具資料的判斷(informed judgment)而非具體的證據(concrete evidence),法院更傾向尊重國會和政府對反恐工作的判斷和意見。
有人認為政府總是誇大國家安全的威脅而過分反應,但是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是恰恰相反的,正是因為以往人們及政府過分低估國家所受到的威脅,才會導致發生美國9.11、中國新疆7.5暴恐等悲劇發生。人們在事後對這些事件作出評價及分析時,忽略了在悲劇發生前,社會及政府在缺乏足夠信息時,根本無法作出有效預判。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中可以看見,在國家安全受到進一步威脅時,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重視高於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是合理、正當和必須的。「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及加以保障的權利,但是此等自由並不是任意的。當保障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利益大於被減耗自由的代價時,公民的自由權利才可以被加以限制。當然,法院在衡量兩者之間的代價和利益時,必須採用非常謹慎的態度,以在兩者中取得一個平衡。
參考文獻:
(1)Haig v. Agee, 453 U.S. 280 (1981)
(2)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1969)
(3)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 130 S. Ct. 2705 (2010)
作者何建宗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施漢銘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法學學士